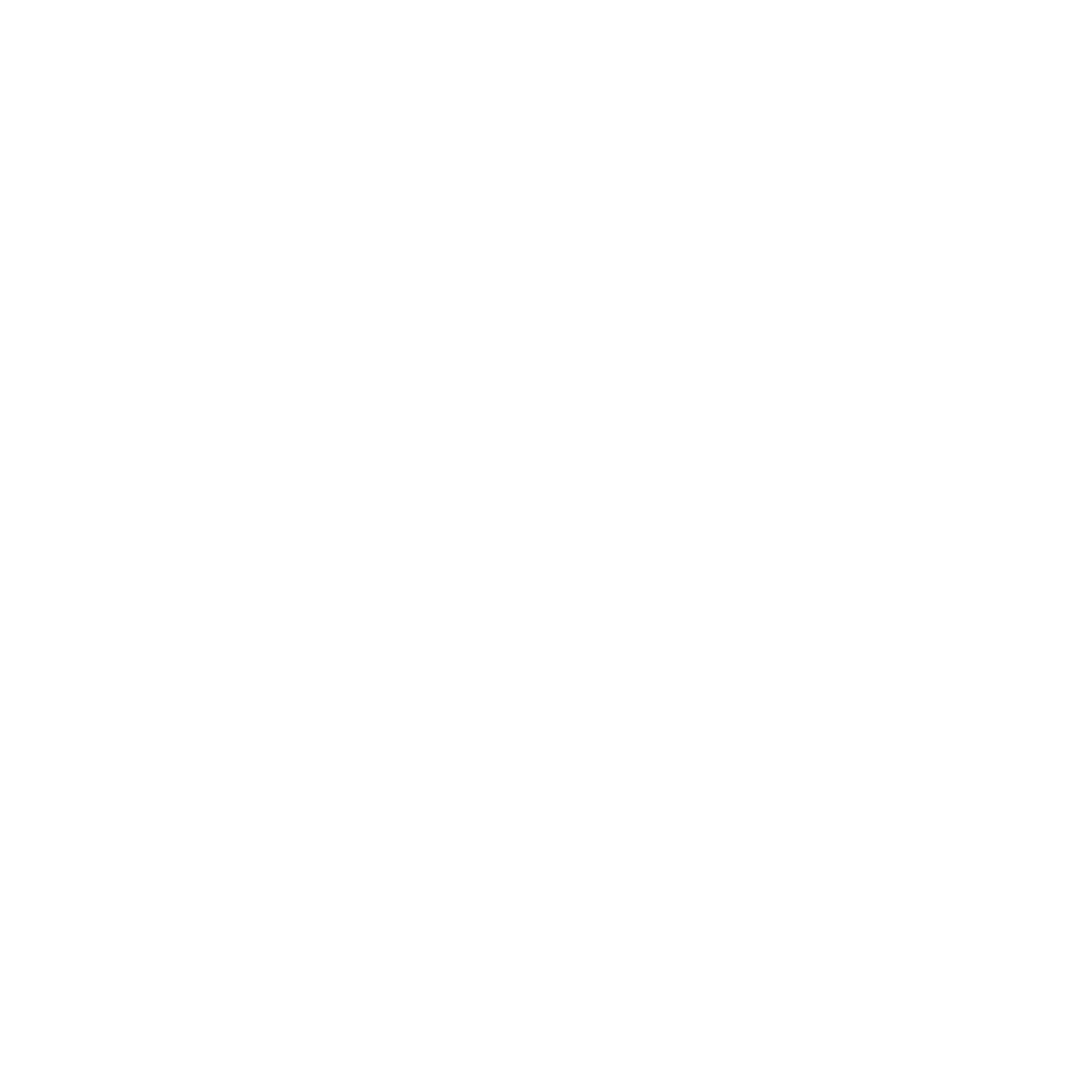一篇流水账————那些流经我的回忆-15
上班暂停(?),回家
八月刚刚过去几天,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学校的艰苦环境,紧急买了票,将所有工作托付在线上,决定回家。仓促做出的决定总得付出对应的代价——我的选择只剩下20h小时硬座,或者在兰州的凌晨独自消磨掉4小时,再挤上凌晨回家的第二趟转乘车。

我选择了后者。低苦艾乐队的《兰州兰州》有句词说明了这种情况,方便回家的火车总在清晨(严谨一点,其实是凌晨)出走。我是晚上12点整到兰州的,第二程车4点才来,所以去哪消磨时间就成了问题。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还在亮灯的凉皮馆子,要了一份凉皮,坐了下来。


可没坐多久,店里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很识趣,为了让店员能够早些打烊下班,我很快打扫完了凉皮,又徘徊到车站附近。最近在读《人生海海》,小说中描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对环境没有一点挑剔,当又看到在兰州火车站附近睡在广场树荫下的大叔时我便又想到小说中描述的那些小人物,好像一株野草,随便栽在哪里都能过活。车站候车室里也有不少横七竖八、以各种意想不到姿势偷时间睡觉的人——为什么是偷时间睡觉呢?我想是因为忙着生存的人们不一定会在赶路的时候有睡个好觉的机会,就只能在换车的间隙匆忙睡一觉。众生百态,这是比较随意的一种,但我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毕竟他们占了候车室的位置。


回家了,除了要适应干燥的空气,还得接着工作。
秋天是忽然间就来临
西北才是第一个体验秋天的地方。一场秋雨,就把气温拉低了10度。


爷爷的花儿落了

七月十一,中元节前四天。天气预报在一周前便昭告了这场雨,所以说它是蓄谋已久,又一次将温度拉低了十度左右。
舅舅的两个孩子乳名分别叫佳佳和圆圆,今年高考结束,终于有空来故地重游。上次她们来这是为了见爷爷最后一面——已是五年之前。那时候的每个春节,总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爷爷奶奶、妈妈舅舅,还有三个孩子就住在老城区的老房子,一起扫除,一起吃饭,一起生活。
老房子的客厅,有一株橡皮树。说是树,其实也就是一盆稍大的盆栽,自二十年前爷爷奶奶生活在这起,就一直忠心耿耿地陪着老人。橡皮树很好养活,偌大且厚的叶片,粗壮且结实的茎秆,即使一周不浇水也能保持活力。老人去世后,这棵树凭借自身的生命力又存活了几年,可后来碰到疫情,封了城,整整半年未给它浇水,就这样它也没能撑过2022年的寒冬。

我们再次到老房子后,除了看到那颗橡皮树倔强的骷髅外,就只剩下一地灰尘。柜子上面压着一片玻璃,玻璃下压着老照片。还是爷爷奶奶、妈妈舅舅、三个孩子的照片,被厚厚的一层灰尘覆盖,已有些褪色。
再然后,又是一次告别,三个孩子各奔前程,妈妈舅舅最终也都决定永远离开这,去孩子们的城市生活。



爱上层楼
八月最后一天,发泄一些负能量。这些话不知与谁可说,遂丢在这里,如果有人不巧发现了这个小条,那么很不幸,你被我赛博殴打了一拳。

该从哪说起呢?还是再说说回家吧,每年回家总能听说那么一个或几个故事,让人不太舒服,却也无可奈何。已是上一辈眼中订婚的年纪,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听母亲讲的——一对精英情侣——均毕业于国内名校,硕士更是就读于常青藤——在被父母抱怨长久不成婚。他们不成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男生在国内找到了工作,女生则留在了海外就业。事实上他们的感情很好,因为一旦有假期,不是男生坐飞机去美国,就是女生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先是回到北京的家,然后再转机寻爱郎,似乎这四位数的机票在他们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其实令我惊讶的不是他们能够经济能力破除异地限制,而是收入如此高的情况下还能抽出假期——在国内读研的最大体会,就是没有假期,即使名义上回家,也得工作,同时也没有收入。哦,对哦,他们是精英啊!我可不是什么精英,我又如何才能想象得到他们的生活呢?
精英,上次听说这个词还是在高中。高中我在某个十八线小县城的高中普通班就读,在学校里都是最底层的存在——竞赛轮不到我们,新桌椅轮不到我们,单独辅导也轮不到我们。那时候我认为,一墙之隔的尖子班应该都是精英吧,我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下晚自习后都有家人开汽车来接他们回家。我那时也确信我不是精英,因为母亲经常加班到后半夜,家里也没什么汽车。我不喜欢集体宿舍,就独自骑行4km回家,那时候啊,自行车光爆胎就有三次,更不用提冬天零下20度的气温,但我竟然有勇气顶着这些不利因素继续我的骑行上学路。我也确信我的同学们中也鲜有精英,因为他们多数都选择住校,父母耳朵上都有被冻裂开的裂纹,里面嵌满了泥土。”他们是寒门贵子吗?”我那时候常想,但现在我似乎对寒门贵子有了一点点新的理解:上学很贵的孩子。分数高些的,公立大学,学校有补助;分数低些的,有了助学贷款,可能还需要在亲戚处秋风一二。毕业后呢?当然是考研,然后失利,再然后,匆匆忙忙找个包吃住的工作,勉强落得住脚。

既然回校准备奋斗了,那么就再说说返校吧。返校,免不了要坐火车,那就免不了要排队,要和一群陌生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隔几分钟,人群向前艰难地蠕动分毫。下火车后,出站口扶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成都的燥热。一位带着两个小孩的妇女,径直走向了队伍最前面,恰巧插在了我的前面——因为只有我在看到他们想要插队后稍停了停,给了他们插队的机会。“绅士一点吧”,我想,他们应该比我艰难,毕竟是妇孺,教科书式的弱势群体。可没想到,这位母亲插了我的队,却没有继续往前走——因为其中一个孩子没跟上。这一举动直接停滞了后面所有人的动作。在我身后的人可能因为我纵容插队的行为表示不满,继续推搡我,我也很识趣,没有继续让着这位带孩子的妇女,托着自己的行李箱艰难地挤到了她的身前,进入了扶梯。
风波没有结束,在出站检票口又一次目睹别人发生口角。这次的主角是两位弱势群体,一位与我年龄相仿,女大学生,一位则是中年妇女。女大学生在我前方3个位置处,指责中年妇女插了队,而中年妇女也不甘示弱,大声斥责女大学生没有礼貌,甚至伸出手想要打人。我必须承认在某个瞬间我是支持女大学生的,我想要在中年妇女伸出打人的手之前跨过去挡在大学生身前,或者说加入斥责的队伍,斥责中年妇女“插队还有理了”。但话头到了嘴边又被咽了下去。某种直觉告诉我,这种事情发生时,最好高高挂起,可回校的地铁上,我又在懊悔,哀悼——为我死在进入大学时就开始死亡的正义感。

正义感的死因是一些星星点点的刀口,握着刀把的正式一些切身经历。整整一年前我就遇到过相似的情况,菜市场,排队购买低价蔬菜。出发前,我就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一定会被插队,因为低价蔬菜少不了咄咄逼人的中老年人。果然,排在我前面的中年妇女身后,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成年男子和这位成年男子的某个女性朋友。看来,他们很熟,熟络到可以为彼此干不道德的事——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不顾身后排成长龙的队伍,给别人占位置。我按耐不住将死的正义感,谴责了他们不道德的行为,于是被数落:年轻人,一点事都不懂。
我想他们所说的懂事,应该就是对类似的事情持纵容的态度吧。只是,初入现实社会的新鲜血液们总得画一些时间为自己的正义感献上黄菊花,然后做好未来埋葬幽默感、新鲜感和道德感的准备。
成功返校了,但是非常不顺利,在一个纵使是凌晨时分也有30度的地方空调失修,于是平均每日的睡眠高达4小时。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