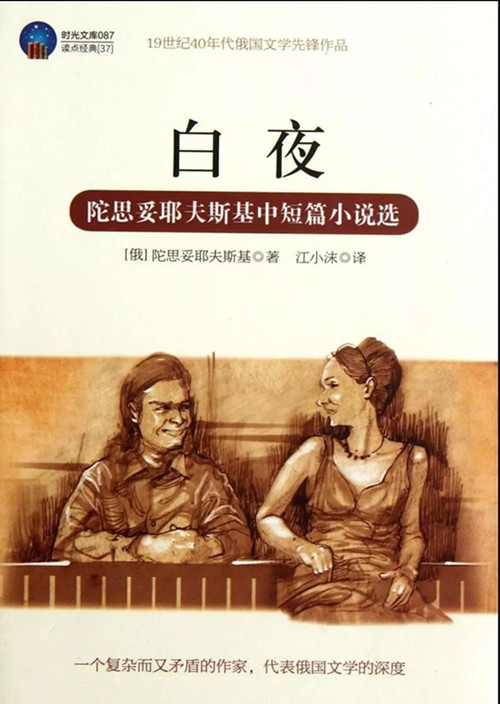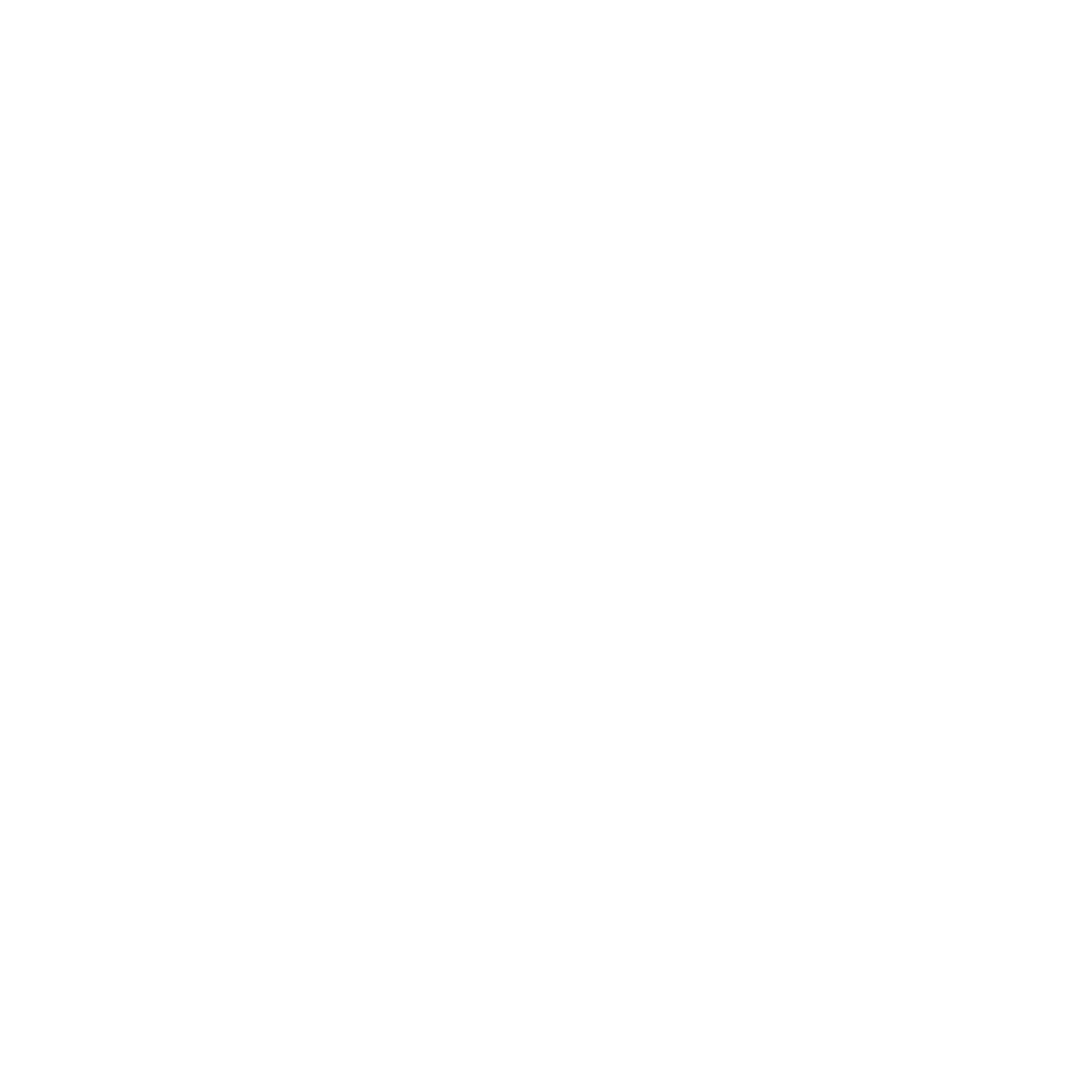四十来岁
任何事物被人铭记,都是因为它有对应的价值,就算没有价值,至少也得有点别于常人的特征。他的邻居——同样居住在高楼最上层的左户,很容易被街坊认出来,因为那家伙有着看一眼就难以忘却的高高隆起的额头;他的对门,在很久以前的旧时代经常被人当作是朝圣的地方,因此故人留下的东西让这一户也有了足够支撑生活的基础;他的楼下刚好是采光最好的一户,那儿的住户刚好赶上了选房热潮,又刚好选中了最抢手的位置,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可他到底有多老,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因为他有二三十多岁年轻人的相貌,但有时候行为却如同60岁的老人一样缓慢老气——索性取个中间值四十来岁吧。总的来说,在整个楼里,他绝对是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人记住的那种类型。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给大伙看看的,是他家里那些旧壁画,可这些壁画也被他珍藏在了阁楼的角落,客人想要看看,就一定要穿过他家客厅长长的走廊,直到整间房子的尽头。阁楼到处都是尘土,偶尔路过的一阵微风都能让那些灰尘在清澈的阳光下起舞,对此他的解释是:经常打扫,但灰尘太大,刚收拾完,就又恢复原样了。

他是有价值的。除去阁楼上的那些老物件以外,他的价值还可以来自他家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就在那条长长走廊的边上,进门时的门槛可能还会意外绊你一跤。那小房间已有些年岁了——不知道破败感是时间太久而导致的,还是由于长久疏于管理,总之这里充满了老气,和他的年龄不总是相称。“这里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上次去那个小房间时他这样说。


他没说谎,40年前,这里热闹非凡。就在那个小房间所在的位置,他找出了许多黑色的金子,大家都说那玩意很实用,能烧,能做工具,甚至能铺路,没准能成为改善全楼居民生活的关键。“那时候大家伙都缺钱啊!”他点上一颗烟,抖了抖肩上的老羊皮大衣,缓缓说,一边拿出了一厚沓黑白照片。照片的内容各异,有一伙人聚在一起画图纸的,有一团人拼命拉纤绳的,还有一群人在泥浆池里拼命扭动身子的。能看出来,照片背景和那个小房子很像,唯一不同的是现在那里难以掩饰的颓势。“照片上那些一起拼过命的人们,在那之后去了其它地方,据说这栋楼上又有好多住户家里也找到了这种黑金,那些住户需要经验和工具才能完成开采。”


他是受过伤的,尽管别人不容易看出来——或者说他不愿意别人看出来。可以尽情用粗犷来形容他,黝黑的面孔、突出的颧骨、老烟民标致的一口黄牙,脸上的裂口里好像藏有泥土,就连耳朵上也有很多条裂缝;和别的住户相比,同龄人总打扮得比他体面得多,但也别不信,他相貌看起来真只有二三十岁,只是长年累月的劳动让他略显硬派,和别的二十来岁的住户一样,他做事干净利落,走起路来像是一阵风。“我又不需要见人,衣裳么咋么个穿那也是我的自由。”于是,迷彩服、深色棉裤就成了他的日常穿搭,由于家里总是尘土弥漫,身上也不免沾上一些,这让他和大地的契合度又上升了一些。

不修边幅也让他付出了代价,那就是那些体面的邻居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家里鲜少有客人来访,就算来了,人们也很少在他家里逗留——他们抱怨那里的尘土和干燥的空气总让他们打喷嚏,可让他看起来孤独的因素并不在于这些。就他自己说,他有很多子女,但都去了其他地方安家,他似乎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那套老房子,自然不鼓励孩子们回来住。他说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孩子们以后能离这个家远点,远点的地方比家里更有机会,就像多年前他鼓励那些开采黑金的工人们去更需要自己的地方一样。你问他怎么办?对此他的回答是:等自己的活干完,也会搬离这里,投奔自己在外打拼的孩子们。


他总是起的早,睡得还晚,也许这也是没多少人愿意来拜访他的理由之一。在他家里,你总能在早晨6点前闻到牛肉面的香味,他说自己就好这口——一清(汤清)、二白(萝卜白)、三红(辣子油红)、四绿(香菜绿)、五黄(面条黄亮),早晨吃一碗能顶到中午,这绝对是体力劳动者的福音。到了中午,他就坐在田埂上,摘下一个西瓜,用手劈开,泡点馍馍进去连果肉带果汁全部吃完,就完全补充了一个早晨流失的电解质;到了下午,老牛怎么也没想到,他又和自己杠上了——晚饭是牛肉小饭:名字是饭,却吃的是面,喝的是汤。


说了这么多,我也该走了。我很感激一直以来他对我的照顾,虽然不是面面俱到,却也足够令人怀念,但我还是没有留下来的理由——这一点就和大多数离开的人一样。
那次出走时是清晨,金塔的胡杨开始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