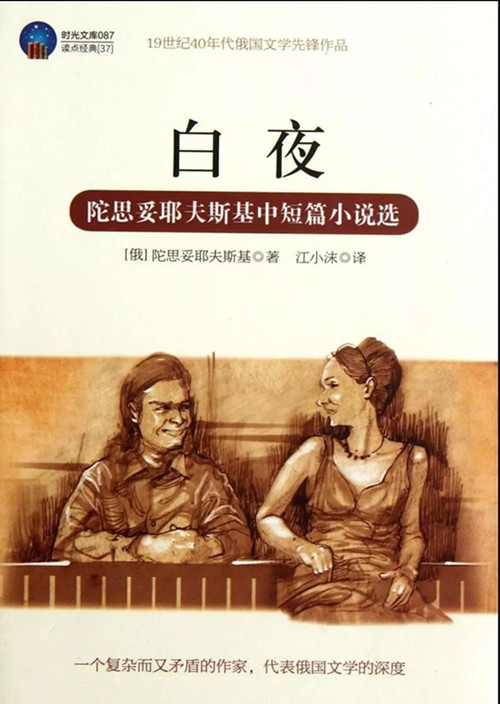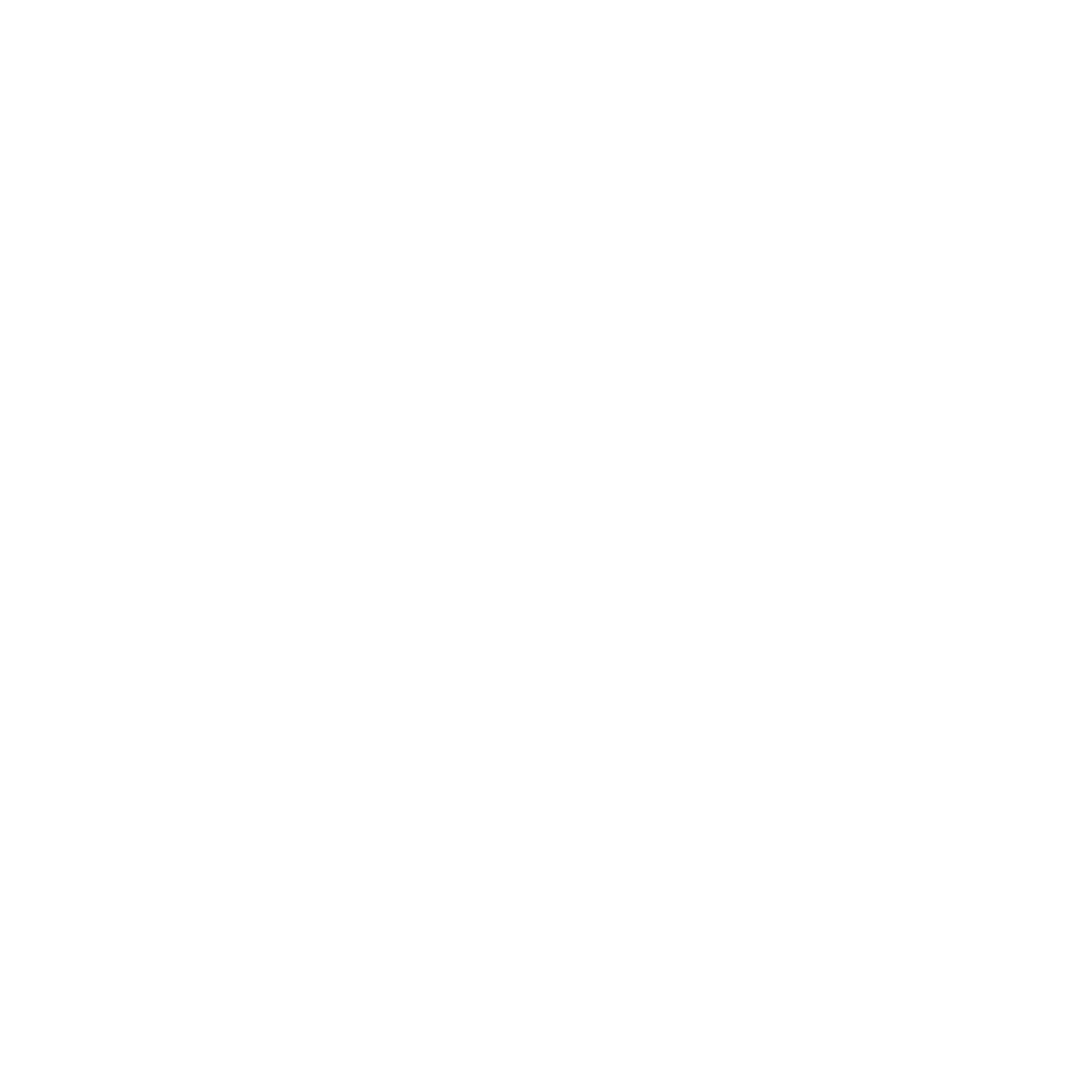一次等于没有
陇椒去籽,切成小块,千万别碰眼睛;鸡胸肉切成小丁,加入盐少许、生抽、料酒、蛋清、切好的陇椒以及锁水分的玉米淀粉腌制20分钟;冷锅热油下入鸡胸肉,煎至变色,捞出备用;热油炒熟陇椒,加入鸡胸肉,老抽调色,少许盐调味,装盘。
锡峰饿醒了,可他居然变成了一只白羽鸡,一只待宰的白羽鸡。这天是五一劳动节前一天,鸡场老板特许锡峰在接受宿命前再去看看世界,看看作为一只白羽鸡在45天生命里未能看到的东西——从出生到成熟,白羽鸡用不了45天,事实上往往比不上绣球的花期。在出发前,锡峰心里有很多疑问:可以假装自己其实是学校里不劳而获的猫咪吗?可以假装自己是公园里自由的鸟儿吗?可以假装自己是每天挤早高峰地铁的社畜吗?——鸡为什么要坐地铁?这不符合逻辑啊。可要是这只白羽鸡会RAP呢?
不管怎么样,锡峰还是跟着一个年轻人出发了——鸡场老板说这个年轻人是买下锡峰的客人,但他暂时不会吃了锡峰,相反他会带着锡峰走完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个年轻人瘦高,穿着维修工的统一制服,讲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出发前他和锡峰的老板(或者说,前老板)谈了很多事情,从五一假期的游玩计划到攒钱给未婚妻买婚戒都讲了一遍,然后随手把锡峰塞进了他的大挎包里。
年轻人的挎包里都是些硬邦邦的工具,扳手、螺丝刀、塑胶水管、火药枪…一应俱全。锡峰有些不舒服,因为他不得不和这些冷冰冰的铁家伙竞争空间,偶尔还能感觉到钉子在扎他的屁股。锡峰不得不靠在挎包的最端点,借着挎包拉链渗漏进来的时明时暗的光,他看到包夹层里是年轻人的高空作业证,只是已经过期一年。第一站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客户,31楼公寓,他需要承担这家人空调的安装工作。年轻人打开挎包拉链,拿出了所有他需要的工具,可当锡峰还在以为终于能换一换狭窄空间里的空气而高兴时,年轻人很快就将拉链拉了回去。隔着挎包,锡峰听到了熟练的系安全绳、登上窗户的声音,然后就是火药枪钻孔、铁锤砸钉子的声音,还有年轻人呼喊这家主人帮忙抬机器的喊声,为了给自己壮胆,这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
后来的事?锡峰没注意。因为装空调的过程过于无聊,在挎包浑浊机油气味的空气里他早就昏昏欲睡了。总之安装没成功,小区物业以安全之名,一定要年轻人出示高空作业证,在主人和物业协调的过程中,年轻人似乎在31楼高层外悬吊了20分钟。锡峰还听到,年轻人白跑了一趟——高空作业的补贴没拿到,还折了引流用的水管,不出意外,这部分又要从他工资里扣除了。
最后一站是菜市场,此时已是晚上9时,菜市场里正热闹,年轻人打算为假期第一天的大餐准备些辅料。锡峰看着整整齐齐躺在展柜里同类,锡峰产生了总体性的、方位性的迷惘。他想起米兰昆德拉曾引用过的一句德国谚语:“Einmal ist keinmal.”如果硬要给它加一句解释,那就是“一次等于没有”。都是第一次路过人间,锡峰被年轻人掐住,而年轻人似乎也被别的什么东西掐住;年轻人必须接受他被掐住的命运,而锡峰此时也不得不接受他被年轻人掐住的命运。这些事只会发生一次,锡峰被吃掉之后,他的口味不一定被年轻人记住,而又会有多少年轻人在不断下沉的生活中被磨平棱角。重要吗?反正也不会有人记得,年轻人一年后肯定不会记得自己前一年的五一假日吃过一只鸡,尽管锡峰曾经想象过很多关于自己作为白羽鸡的最终归宿:自己的腿被送往肯德基,裹上面包糠炸好;胸肌被送往超市,放在铺满冰块的桌面上;脚被嘴馋的外国人卤掉,就着《瑞克与莫蒂》被吃掉;翅膀被送往火爆全平台的吃播面前,被快速炫干净。
锡峰又饿醒了。